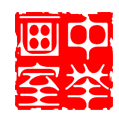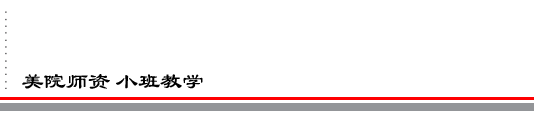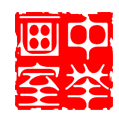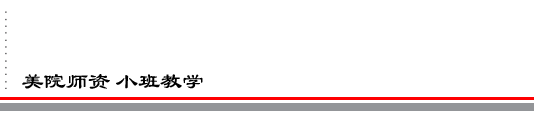承家学渊源,陈醉少时饱读诗书,抚琴习画,且因父亲戎马倥偬的不乏射骑精神的潜移默化,可谓“六艺”皆备。青年时,于大学追随敬业良师,刻苦学习绘画艺术。学成不久却赶上文革动乱,以致在“下放劳动”的“待遇”中,把沉甸甸的底层生活“课本”啃读一遍。1978年,命运垂青,陈醉在竞争中以优异成绩,考中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成为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陈醉如鱼得水,学术与艺术并驾齐驱,一路辉辉煌煌,由“我要当总统”的稚子之愿,到“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的青年大志,早先就奠定了陈醉文化眼光的高远取向。后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形式感”和“裸体艺术”的深入探索,则为其文化眼光注入更加明确的理性因素。概略地了解其学术的追求,对认识陈醉绘画艺术的神采无疑是必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揭示,为本世纪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只有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才能保障文明的进步。因此,人类发展的历史,乃是人被压抑的历史。在此历史中,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存在,情欲、幻想、激情和希望等丰富的人性构成,则被逐出理性的现实,归入文明的禁忌或心理学的冷宫。如何解放包括情欲在内的丰富的感性世界,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便是以批判和改造压抑文明为己任的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
椐天津画室总体来看,陈醉的学术思考,属于文化哲学一路。拜读他一系列的学术著述,尤其那部影响深广的《裸体艺术论》,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他表述为“文化超越”,赫然纸上,通篇贯穿。然而,陈醉的学术贡献不在于他以独立思考策应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哲学思潮,而在于他立足中国文化的现实,把“文化超越”这一主题,径直导向被现实原则严密封堵的千古禁区——性意识和裸体艺术。这本身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年《裸体艺术论》的出版所产生的核爆炸似的影响,便是一个明证。更重要的是,陈醉秉承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把艺术和人生问题相联系,使自己的学术思考以至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人生实践价值。锐利果敢的学术思锋,使陈醉相信人体美是人类对自身的审美感受,却特别强调这种审美情感的物化实践,即裸体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始终是与人的潜意识欲望和性意识紧密关联的。正是因为它永远保持着与现实伦理既互相冲突又互为余补的微妙关系,裸体艺术才具有一般艺术或现实人体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别而又永恒的文化功利。对此,陈醉表述为“欲望的升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或“人生情结的解脱”。即如他所指出:“裸体艺术,是人对自身审美感的物化,它是对现实人体文化的超越,以前者更上升了一个层次,不知多少人生情结,在这里得到了解脱!显而易见,陈醉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以颠覆现实的偏激去寻人性复归的出路,而是慧眼识得现实生活可以拥有的“更高的层次”。在他看来,这个足以寄托人类更高理想的层次,由“欲望的升华”即“一种文化的超越”所构成,它的现实形态便是艺术。具体到人类感性世界的情欲或性意识方面,那就是裸体艺术。在陈醉的学术视野中,艺术不只是审美的,还是有文化功用的,是诉诸审美的人生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深刻之见。
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考,作为意蕴深刻的理性成分,构成陈醉文化眼光的主体。凭着这种眼光,他不仅把“文化超越”的主题写在自己的著作上,而且将它表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在一定意义上说,陈醉的绘画创作,是其“裸体艺术论”的继续和展开,是其对艺术文化功用的验证和发挥,是其追求“欲望的升华”或“人生情结的解脱”的自我实践。他曾用“苦恼时的创造”一言概括自己的作品,其绘画创作的价值取向是自觉和鲜明的。在天津画室看来,陈醉80年代以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即追求“文化超越”的。但是,与一般主题性绘画力求物化思想概念的旨趣大不相同,陈醉绘画的“主题性”不是强调对某个确切概念的表现,而是将这种表现本身或者整个绘画行为本身,作为“文化超越”之实践主题的贯彻与实行。对他来说,画画和画面的形式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自身。即如他的坦率表白:“我的一些作品,大多不是为了竞选展览而去绘制,所以对诸如题材、主题等‘常规项目’并未认真推敲。…更多的往往还是出于抑郁的排遣。
本着别样而意深的“主题性”追求,他的作品包括油画和国画,尽管不乏情节性的具体描绘,却无法归结到某个思想中心。只因为在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的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着意于心灵世界的排遣,特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在流动的情感体验和静态的形式结构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陈醉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索,并颇有心得。他的代表作《空间,我们的》(油画,1982)和《熔》(油画1982),最初的画面是对留有美好记忆的自然景象的再现,然而实际呈现的具象“风景画”效果,却让画家深感“词不达意”。几经修改,仍不满意。后来,于琢磨中逐步将原先的自然形象抽象、幻化、“直至觉得寻找到了构成与心灵的透明点的时候,再一气呵成地将它画出来”,(《苦恼时的创造》),于是成就了目前的这种理想效果。他所找到的那个“透明点”,正是心理时间与形式空间的最大程度的契合。出于这次成功的探索,他80年代创作的大部分油画,多取抽象手法或表现式、印象式手法。显然,陈醉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绝不是唯表现形式的,而始终以“升华”、“净化”、“解脱”等绘画目的实现为准则。
陈醉不同凡响的绘画价值观,使他在追求自我理想目标的创作中,并不计较家派手法的纯粹性和构形逻辑的一贯性。在这方面他显得非常灵动,颇为“意识流”,甚至会不知不觉地顺随性情自动而形出偶发。《火祭》(油画,1985)一画,手法来源甚为丰富,它综合了写实主义的造型、表现主义的笔法、印象主义的色彩以及象征主义的构思和寓意。在画面上,画家唯我地调遣各家各派的手法,让它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并最终统一于、圆满于“我”的“文化超越”。就创作手法而言,最能体现陈醉个性的作品是《追思》(油画,1986年)。据画家自己介绍,在最初的草图中,他只画了一对抽象隐约的手。然而,画着画着,就多出了一只手;再画着画着,又多出一只手…等到作品完成时,线条交错构成的画面竟出现了五只手。手的“自动”增殖,不免让画家心生疑窦。但绝妙的是,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画面,却有十分完美的效果。得意于出乎意料的成效和美好的过程体验,他权当一切是潜意识的驱遣,而不劳追根问底。现在来看,发生在陈醉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偶然现象,自有必然之理。把人生问题诉诸审美解决的绘画目的论,自会使陈醉“沉醉”于绘画的展开过程,以致画笔不知不觉地随着心绪的流动漫游,在画布留下突破理性“草图”的灵动之迹。所呈迹象何以为手形,那只能说画家心中积郁了许多未曾释怀的关乎于“手”的人生情结。就这一点,我依然不敢打探他究竟为何的心理秘密。但我相信,陈醉作此画时,真的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陈醉,沉醉矣。
以画为目的,固然比以此画为手段更利于也更需要达到这种大化之境。即便如此,要以油画取之,难度还是很大。此非画家不能也,乃油画“天性”之限也。油画对作画物理时间的相当要求,似乎注定它是为“写实”而存在,它不善于接纳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陈醉在《苦恼时的创造》文中,坦述过自己面对面布却不得配合的深深的苦恼——他恨不得将一番惆怅洒落画布,画布却说:“先生,您得慢慢地来。”这种感觉真切而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画家日益高涨的“意写”心气,自然与之相去甚远。也许这是原因之一,陈醉于90年代更多地投入国画创作。学贯中西的陈醉,以前也画国画,只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国画的“写意”品格有了更新的认识。凭着不断锐化的文化眼光,他洞察了国画的写意性与“文化超越”主题的默契。这种默契,于“升华”、“净化”、“解脱”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自我实践,无疑深具价值。于是,陈醉欣然向往,全力以赴,创作了一大批兼具审美意义和人生实践意义的优秀画作。文章来源:天津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