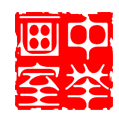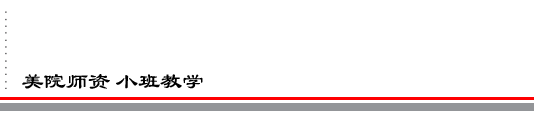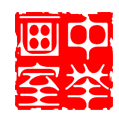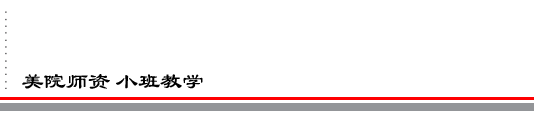天津画室告诉我们在艺术创作中,只有一种方式可以阻止丑循环复制,那就是让美的对立体在结构、形态、线条、颜色、阴影、词汇、声音等等物质的或文化的介质中休眠。不过,谁要是采用这一方式,谁就得首先让自己的天才休克。确实有一些极少数的艺术家,他们宁愿把生命交给邪恶,也不愿让自己拥有一个正常人的称谓,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天才抵押给丑恶,也不让自己获得一个一些平凡的人们十分容易理解并时时赞美的好名声。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到丑恶亲近艺术和艺术需要丑恶。
梵高的作品在运用这种方式时,虽然显得十分谦和,但是在他用大量的明黄以及十分不明确的线条努力地解散艺术作品必须涉及的一对关系时,他的颜色比他大胆,他的线条比他狂妄,甚至他的绘画工具比他本人的表现要坚定得多。这有一股力量来源,生命只有历经了邪恶才健康,生命只有经历了丑恶才能创造美,生命只有饱受痛苦、贫穷、失望、压抑、孤独、欺诈、禁痼、无望,才能珍惜美对于人类的价值。梵高对于平凡人害怕并极力回避的事物虽然只保持冷淡的尊重,但是就特殊职业而言他相信,“画家的生活中有不幸、烦恼与痛苦,对画家来说也有好处,因为其中包含着善意与真诚,包含着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游出欧洲“信仰之海”,坐在海边发出的带喘息的挑衅。不过,一些使用语言来表现他周围环境的艺术家,在采取这一方式时,情绪就不那么好控制了。评论家说,整个十九世纪的丑恶美丽得像鸢尾花一样,那种季节性复制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文明勋章,他们在拨开整个时代的光辉而在寻找的仅仅是一份证明,比如洛特雷阿蒙,“我寻找一个和我相似的灵魂,却没能找到。我搜索大地的每个角落,我的恒心无济于事。然而,我不能总是孤独。应该有人赞同我的性格,应该有人具备和我一样的思想”。 十九世纪不可能给人提供社会行为证据,诗人也不可能找到一份丑恶相同的证明,没有好脾气的诗人表现极大耐心后,直接让语言归顺了丑恶,“当然,直到出现晨曦——它即将来临,我不拒绝你的床铺,它配得上我。我感谢你的好意…掘墓人,凝视城市的废墟很美,但凝视人类的废墟更美。”显然,艺术家对自我的仇恨是因为仇恨自己无法接受丑恶。
天津画室给大家建议面对十九世纪,使用颜色的人与使用语言者不一样,即使他发现没有一个人与自己的思想相同,他也没有企求外界赞同他的性格,更不企求他人和自己一样对世界保持愤怒。他只是对一切感到奇怪,“每当我们看见不可描绘的形象和无以言表的凄凉——孤独、贫困和悲惨,万物的终结和极致,上帝进入一个人的心灵,这总是能撞击我,总是非常奇怪(引自梵高的信)。——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在别人认为上帝死了的那个世纪,他最多以为上帝去别的需要他的民族旅游去了,而无暇顾及已经够文明的欧洲。他的心灵总是敞开着,随时期待上帝回来,并把一切自己内心的激情和画笔的突破归功于上帝。
——这是他对抗一切的力量源泉。被我们理解为他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从《夜间咖啡馆》和《夜间露天咖啡座》这两幅作品中,看到的只是颜色和视点出了问题。他一向为外人所铭记的主观咸受能力和常常失控的情绪,在这两幅画中无法寻觅,他甚至像一位主张价值无涉的哲学家一样,那么冷酷地去个人化,——当然,虽然梵高在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和书信中透出深邃且另类的哲学思考,但在画中绝不摆弄这样的哲学技巧,更不允许在自己的作品中夹杂这样的非艺术的成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代表更多的人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印象。文章来源:天津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