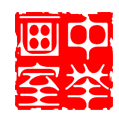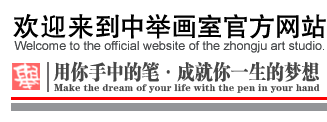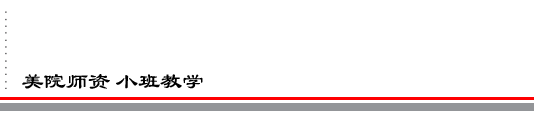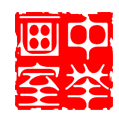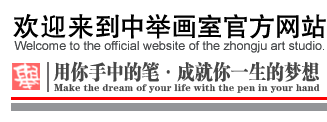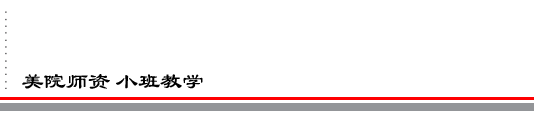女性绘画是否存在?一直是中外美术批评的焦点,男权文化观者认为不存在什么女性绘画,即便是女性画家的作品,也是模仿男性绘画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没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因而在历史上也就一笔勾销了女性画家的成就。西方70年代新女权运动中的女艺术家,不仅为争取展览、出版、宣传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展开了斗争,也为历史上的许多优秀女画家的被埋没而鸣不平,并为发掘历史上不该被遗忘的女画家做着不懈的努力。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杰出的女画家,并在美术史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同样在男性编纂的史书中被偏见、片面所忽略。因而发掘历史上那些“失落”的女画家及其绘画作品,并给予恰当的历史评估,修正以男性为主宰的传统绘画史的片面性,正是女性绘画批评的任务。
女油画家—历史的“失落”
天津画室据知中国油画有近300年的历史,在清朝康熙年间郎世宁等传教士及通商口岸外籍油画家的影响和传授下,中国人开始了学油画、画油画的历史,这前200年的历史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断裂。今天作为一大画种的油画,是“五四”前后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改造旧文化直接从欧、美、日等国先后引进,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油画发展的路。
其间女油画家受新思潮的影响,带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走出封闭的闺阁,投身到新文化的社会运动中。她们中不少也出国留学,回国后与男画家一起为创建新的油画文化作出了同样的贡献,然而在油画史上女性同样“失落”了。当今人们都知道有个潘玉良,并不知道她是中国早期西画运动中杰出的女油画家。她那绚丽、浓烈的油画色彩,泼辣、洒脱、豪放的用笔,在二三十年代还普遍缺少色彩感的早期油画时期,她以女性对色彩特有的敏感,深得印象派色彩的奥妙,曾被时人称为“中国印象派第一人”。而对她艺术中所流露的苦涩、压抑的悲剧情调及桀骜不驯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内涵就很少为人理解,尤其对她作品中所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更无了了。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她曾为妓的传奇经历。出生名门的孙多慈也因为她与其师徐悲鸿有一段感情纠葛而常被人作花边新闻提及。
而她对艺术的执著,尤其是她能容纳徐悲鸿所不齿的现代派,悉心研究,并有见地地影响了她的学生们,可见她对徐师艺术上的偏颇并不盲从,保持了艺术的独立品格,但人们对此倒并不看重。对于我国早期出国留学的油画家,史家们可以列出李叔同、李铁夫、李毅士、冯钢百、林风眠、徐悲鸿等一长条的名单,惟独忽略了早年出国留学并学业有成的蔡威廉、方君碧、关紫兰等。蔡威廉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之女,1915年(其时9岁),第一次随父母赴欧,后又二次赴欧,毕业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学院,1928年回国任教于杭州国立艺术院,她的肖像画,在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中就“一鸣惊人”。
她虽没有发表如徐悲鸿关于中国画改良的宏论,也没有发表像林风眠关于中西调和的理论,但在她的艺术实践中却始终探索着中西艺术相融合的道路,并有不少佳作问世。关紫兰1927年就留学日本,人东京文化学院,作品多次人选日本“二科美术展览”并举办过个人画展,深被日本油画界推重。1930年回国执教,当时曾有人评论她的油画“有宝石一样晶莹玉润的色彩,有小鸟一样活泼的笔触,有天鹅绒一样温馨的画面”。另一位1924年就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周丽华,30年代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时人对其艺术上“新的形式”、“优美的线条、温丽的色彩,深刻感人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当时大多数油画家还难以把握多人物大场面的油画创作(仅有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篌我后》,林风眠的《人道》、《痛苦》等巨幅油画问世)。而蔡威廉此时也已创作出了《秋瑾》、《天河会》巨幅油画,前者颂扬秋瑾英勇就义的悲壮,张扬作为女性的民族英雄的历史价值;后者借神话故事来表达女性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愿望。她的作品显现出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方君碧早年就学巴黎朱里安美术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转波尔多美术学校,后又毕业于国立巴黎美术学院,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女学生,1924年她的作品入选巴黎沙龙,名声大震,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1925年回国执教,为岭南派所推崇。战乱年代,她不畏艰难,仍能勤奋作画,作品中反映出母亲失子的痛苦、妻子失夫的困境,真切地表达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情感经历。还有一位是“决澜社”的女成员——丘堤,这个代表着中国早期现代艺术运动标记的画会,把唯一的一个“决澜社奖”的荣誉,给予了这位女性艺术家。她的富有装饰性的油画在当时还引起了论争。解放初从法国回本土的云南女画家刘自呜,虽在写实绘画一统天下的时风中,又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却始终不改融中国写意绘画于油画中的探索之路,顽强地保持了艺术的独立品格。
天津画室在这不再一列举,但可以看到,这些中国早期油画界中的女油画家,她们以自己不同凡响的艺术在当时脱颖而出了,闪耀出了耀眼的星光。文章来源:天津画室